
“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专题讲座顺利举办
7月1日下午,平子友长(Tomonaga Tairako)教授受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邀请,为学院师生作“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的专题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刘庆霖主持,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预聘副教授王聪聪,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汪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助理教授陈绍辉参会与谈,十余名本硕博学生参与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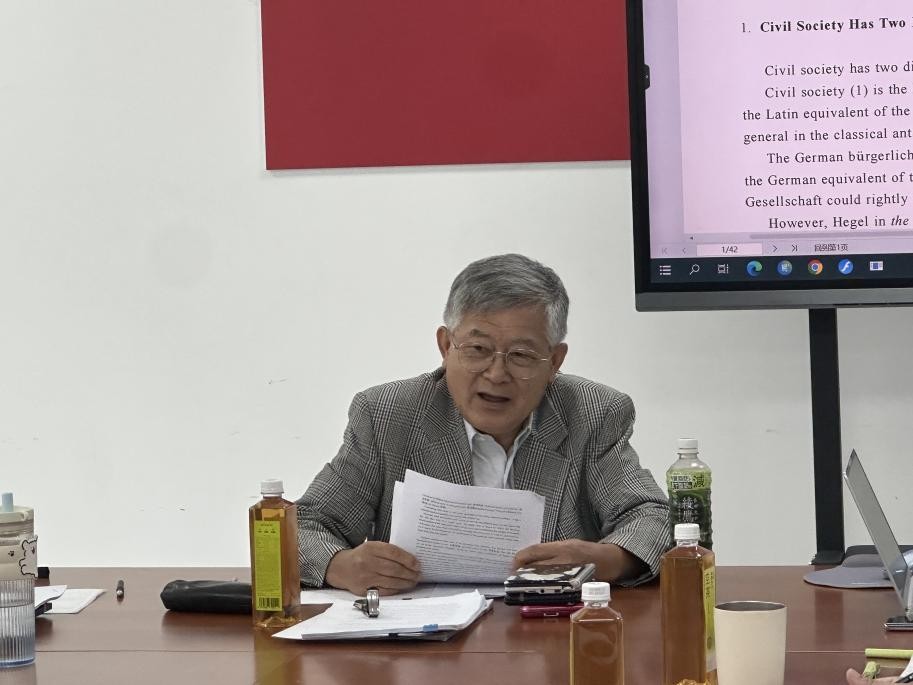
在本次讲座中,平子教授主要围绕以下两个主题展开论述:
- “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论发展史——从亚里士多德到葛兰西
亚里士多德理论中的“城邦”(polis)是政治意义上的“市民社会”(societas civilis, civil society)概念的起源。亚里士多德将“家庭”与“城邦”,也即“经济”与“政治”鲜明地区分开来。家庭是经济管理的场域,而城邦是政治参与的场域。在城邦中,成年男性公民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随着现代国家制度的出现,civil society的概念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在霍布斯的理论中,他一方面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的做法,从政治意义上理解civil society,将其与civil state, civil government, civil power直接联系起来,认为civil society通过建立国家实现了和平,摆脱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另一方面,摒弃亚里士多德的“家庭”与“国家/市民社会”的对立,认为国家可以从家庭的扩张中发展出来,这一点是霍布斯在关于“自然型国家”的论述中表现出来的。
随着政治经济学的诞生,civil society的概念更加细化。斯密区分了civilized society(文明社会)和civil society。前者是从经济层面理解的国家,是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的国家;后者是从政治层面理解的国家,是保障正义、保护私有财产的国家。就此而言,斯密仍然遵循了civil society的古典传统,将civil society理解为政治社会。但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在斯密,包括霍布斯看来,政治社会的政治体制并不表现为全体公民共同参与的共和制,而是全体臣民服从于单一君主的君主制。
与霍布斯和斯密不同,卢梭在继承civil society的政治意涵的同时,试图恢复civil society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理论中的共和色彩,强调只有公民保持自身作为主权者的身份、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的社会,才称得上civil society。
康德仍然是在政治意义上理解civil society,将其与具有经济内涵的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 society)区分开。更具有独特性的是,康德进一步在政治范围内区分了具有世界主义理想色彩的civil society与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家(state)。
黑格尔是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概念的创始人。黑格尔明确区分了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前者由市民(Bürger)、资产阶级(bourgeois)构成,因而也可以称为资产阶级社会,后者由公民(citoyen,citizens)构成。当然,黑格尔也一定程度保留了市民社会的政治内涵,他指出,市民社会作为政治国家,只是旨在保障和保护财产以及人身自由。经过对立可以发现,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三个方面的独特性:第一,首次将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区分开来,在此之前,二者通常是作为同义词出现;第二,首次将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与国家(state)区分开来,在此之前,人们往往从政治国家层面理解市民社会;第三,首次将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与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 society)联系起来,在此之前,更强调二者之间的区分。
马克思认可并继承了黑格尔理论中具有经济内涵的市民社会概念。当然,尽管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古典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没有发挥显著作用,但仍然以隐性的方式存在于其理论构想中,例如: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社会”概念,以及晚期马克思对于自由与必然关系的理解。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在认识到马克思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概念与古典意义上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概念的区别的基础上,试图重新复兴古典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他的做法具体表现为:将市民社会区分为两层,分别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与作为上层建筑的市民社会,保留和强调市民社会的政治内涵。
- 日本学界对“市民社会”概念的研究情况
二战后,“市民社会”与“市民革命”成为日本重建民主社会的核心口号,旨在对抗天皇专制制度。但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学界逐渐意识到其对“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概念的理解存在根本性缺陷:一方面,大多数日本学者忽视了civil society的古典渊源,错误地将civil society视作区分现代欧洲与旧欧洲的关键概念;另一方面,将civil society与黑格尔赋予新内涵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等同起来,忽视了两个概念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对此,平子教授强调,civil society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作为societas civilis英语对应词的civil society,即政治社会,这是一种具有古典渊源的含义;其二是作为黑格尔之后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英文对应词的civil society,即经济社会。

在与谈环节,王聪聪老师指出,“市民社会”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往往具有不同的理论内涵和现实基础,如葛兰西就区分了东方的“市民社会”和西方的“市民社会”,并就市民社会概念是否是一个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概念?我们如何运用市民社会理论展望未来?向主讲人提问。平子教授回答道,“市民社会”概念尽管是一个发源于西方的概念,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自觉地、带有批判性地借用这一概念。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构想是我们可以用于展望未来的重要理论资源。

汪越老师指出,平子教授的分享对于中国学生了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中的“市民社会”概念具有重要价值,并就市民社会概念的转变是否可以理解为西方社会核心从政治向经济转向的呈现、汉娜·阿伦特和葛兰西对于市民社会的理解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构想对人类解放的价值三个方面向主讲人提问。平子教授回答道:第一,市民社会从政治向经济的转换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仅仅发生在德国。第二,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将人类活动划分为劳动、工作和行动,并强调公共领域、政治领域中的行动的重要性,这是一种与卢梭相似的观点。与之形成反差的是,葛兰西将政治视作霸权,而强调市民社会是可以反映经济需求、形成基本共识的领域。第三,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遵循了古典传统,承认政治领域对于人类解放的重要性。

陈绍辉老师指出,平子教授对市民社会概念的梳理,勾勒出一条从古典政治哲学到现代社会理论的思想脉络,其核心可概括为三重关键转向:从政治共同体到经济社会的语义裂变、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理论关系重构、从理论建构到现实批判的功能转向。此外,陈老师就“如何在现实中协调市民社会作为经济体系与政治参与空间的双重属性?”向主讲人提问。平子教授首先强调,其研究主要聚焦于文本分析、理论探讨,并不直接具有现实导向,进而延伸性指出,政治参与往往容易受到经济利益的深刻影响,而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构想是避免这一点的重要理论资源。

讲座最后,老师们和同学们对教授细致专业的分享表示感谢,讲座在热烈和友好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