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自然辩证法”专题讲座顺利举办
6月13日上午,保罗·布莱克里奇教授受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邀请,为学院师生作“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自然辩证法”的专题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聪聪主持,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田曦,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陈艺文,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讲师李靖新弘参会与谈,十余名本、硕、博学生参与活动。

在本次讲座中,教授聚焦于对“马恩对立论”的批判,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论述:

- “马恩对立论”的源起
教授指出,至少在英语学界,恩格斯作为一位原创思想者的声誉低至谷底。究其原因,第一,在政治层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乐观主义学说,在工人阶级退守和士气低落为主导的西方社会环境中处境艰难;第二,在学术层面,自20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为,恩格斯歪曲了马克思的思想,并成为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源头。
- 关于《反杜林论》的争论
教授指出,《反杜林论》是“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断的主要依据。正是通过这本书,马克思主义得到最具影响力的推广。鉴于此,围绕“马恩对立论”的争论首先聚焦于《反杜林论》,如特雷尔·卡弗等人谴责恩格斯将马克思的革命实践概念简化为“机械唯物主义”和“政治宿命论”。教授对此反驳道,从写作目的来看,恩格斯与杜林的交锋是为了捍卫革命的政治实践;从文本内容来看,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积极态度彰显出他所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
- 关于《自然辩证法》的争论
教授以斯文-埃里克·里德曼(Sven-Eric Liedman)撰写的《矛盾的游戏》为靶子,批判了其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错误解读。里德曼的批判可以细分为三个维度:第一,恩格斯构建了一套理论体系,不仅陷入“科学专门化与体系建构之间的矛盾”,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埋下了祸根。第二,恩格斯从自然推导出社会,模糊乃至逾越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界限,陷入了还原论。第三,恩格斯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捆绑在19世纪即将过时的自然科学体系之中。
对此,教授一一进行了反批判:第一,现代科学研究的专业化,并不意味着其无法被整合为一个更大的整体。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的只是脱离实证科学知识基础去创造体系,而不是建立体系本身。第二,恩格斯实际上是把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理解为一种质的飞跃,即一种涌现的、辩证的关系,因此社会虽源于自然,却有根本不同于自然的独特属性。第三,恩格斯始终强调的是理论与经验的辩证统一,这是一种根本不同于英国式经验主义认识论的立场。

在与谈环节,田曦老师指出,除开《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文本,《共产党宣言》也是西方学者营造“马恩对立论”的文本依据。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e)就认为,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宣言》的草稿和定稿中对于危机原因的分析存在明显差异,恩格斯将其与竞争直接关联起来,马克思则将其归结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我们应该辩证看待这种文本差异所反映的马恩思想互动。此外,田曦老师还就“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方法”向主讲人提问。

陈艺文老师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自然与历史的统一,他们的自然观、辩证法都并非是完全“社会历史的”或者“纯粹自然的”。我们迫切需要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并发展为与当代问题紧密相关的生态辩证法,以便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视角分析人类世危机。

李靖新弘老师指出,第一,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关注的焦点不应停留在是否应该构建体系的问题上,而应深入探讨应该构建何种体系,可以想见,一个开放灵活、能够吸纳科学新知、保持理论生命力的动态体系是具有吸引力的。第二,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迭代的现实背景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价值并不在于某一具体的观点,而在于恩格斯的思维方式、对于变化和矛盾的理解,以及对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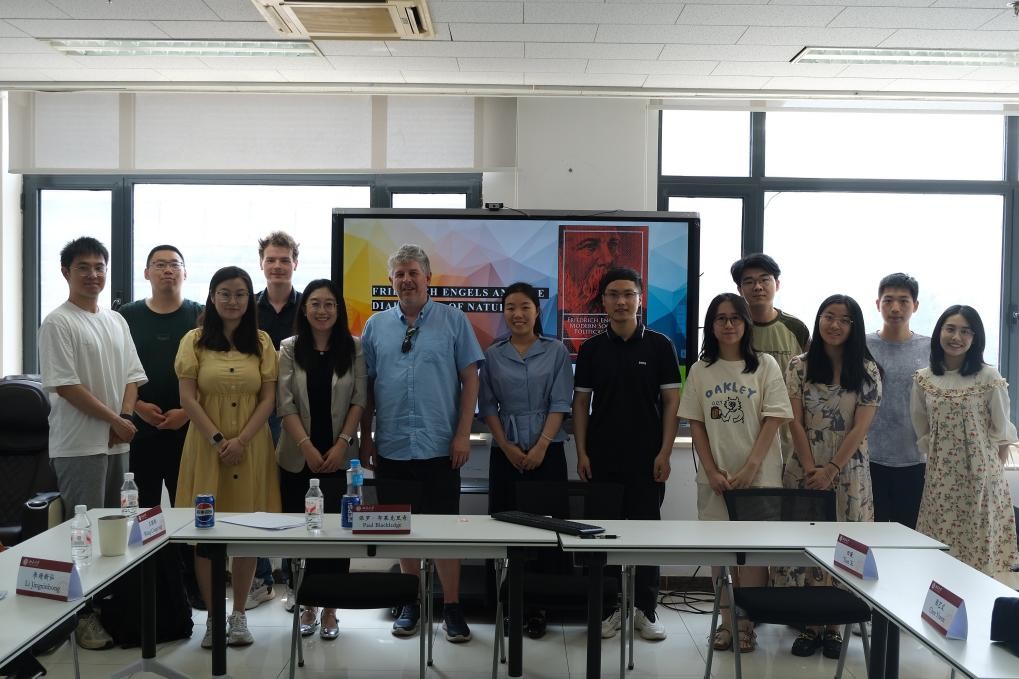
讲座最后,老师们和同学们对教授细致专业的分享表示感谢,讲座在热烈和友好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